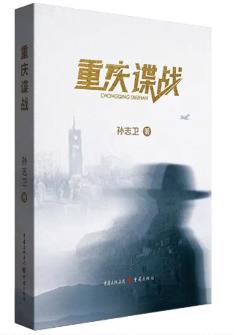圖書(shū)推薦
BOOK RECOMMENDATION

催眠师甄妮
本周,小編將為所有的讀者分享一份女性書(shū)單,讓我們一起聆聽(tīng)女性的聲音,理解她們的故事,發(fā)現(xiàn)她們的智慧,并從中尋找力量。希望每一位讀者都能從這份書(shū)單的閱讀中收獲力量、溫暖與健康,活出更精彩的人生!
今天小編為大家推薦的是《催眠師甄妮》,這是一個(gè)關(guān)于接納自我,尋獲愛(ài)與生命意義的故事。
圖書(shū)介紹
這部長(zhǎng)篇小說(shuō),以敘寫(xiě)甄妮由重度失眠抑郁輕生自棄到自我療愈,成為催眠師救助“都市病”患者,借此尋獲生命意義、重建人生價(jià)值的艱難歷程為主線,疊加了師友閨密繾綣情誼,知識(shí)分子自發(fā)鄉(xiāng)村建設(shè)實(shí)踐等副線,多維度呈現(xiàn)了中國(guó)轉(zhuǎn)型劇變期真實(shí)的城鄉(xiāng)社會(huì)生活。
作者簡(jiǎn)介:
冉冉,詩(shī)人,小說(shuō)家,中國(guó)作家協(xié)會(huì)全委會(huì)委員,重慶市作家協(xié)會(huì)主席。在《上海文學(xué)》《人民文學(xué)》《十月》等發(fā)表多部中短篇及長(zhǎng)篇小說(shuō),出版詩(shī)集《從秋天到冬天》《空隙之地》《朱雀聽(tīng)》《和誰(shuí)說(shuō)話》《望地書(shū)》及中短篇小說(shuō)集《冬天的胡琴》等作品。獲全國(guó)少數(shù)民族文學(xué)“駿馬獎(jiǎng)”、首屆艾青詩(shī)歌獎(jiǎng)、西部文學(xué)獎(jiǎng)等多種獎(jiǎng)項(xiàng)。
精彩試讀
失與眠
2002年早春的一天,甄妮隨葉滋滋的小姨金枝,從杭州飛回家鄉(xiāng)壹江。那時(shí)的甄妮還不知催眠為何物。哀慟與絕望先是擠占睡眠,繼而損毀健康—她眼圈烏青,膚色蠟黃,原本豐潤(rùn)的臉頰瘦削脫形……看上去比閨蜜滋滋更像絕癥病人。滋滋臨終前身體疼得厲害,雖備受煎熬卻鎮(zhèn)定安靜。她對(duì)父母親昵感恩,對(duì)日夜陪護(hù)在病床前的甄妮依依不舍。她對(duì)父母說(shuō),你們不要為我悲傷,甄妮就是你們的女兒,她會(huì)替我愛(ài)你們,也會(huì)替我好好活。葉媽媽早已將這個(gè)溫善真誠(chéng)的姑娘當(dāng)成女兒,滋滋爸卻一直不待見(jiàn)甄妮跟滋滋走得太近。滋滋住院不久,甄妮也患上了罕見(jiàn)的瘙癢癥,于是開(kāi)始以鉆心的癢陪伴滋滋的疼。滋滋不時(shí)去摩挲甄妮的手背:不是止癢,是止抖顫,但無(wú)論怎么克制,她的身體還是不由自主地抖個(gè)不停。滋滋虛弱地苦笑:“看看,我的疼都成你的癢了呢。”其實(shí)她明白,甄妮的癢是她內(nèi)心的苦痛化裝而成的。滋滋的時(shí)間本來(lái)會(huì)更長(zhǎng)一些,但她不想再拖延,說(shuō)是疼得實(shí)在受不了—實(shí)則是心疼甄妮。甄妮太痛苦太難受了,所受的煎熬一點(diǎn)不比她自己少。滋滋走得平靜。臨行,她調(diào)侃說(shuō),自己的生命太過(guò)完美,再不走,難免影響到人間的公正。她帶著滿滿的愛(ài)和祈福上路,甄妮卻痛不欲生。送別滋滋的第三天,處理完個(gè)人事務(wù)的她服下了超量三唑侖。金枝發(fā)現(xiàn)甄妮赴死事出偶然—當(dāng)晚她倆通過(guò)電話,收線后金枝突然覺(jué)得對(duì)方狀態(tài)異常,于是再度撥打小靈通,可一直是忙音—直覺(jué)告訴她肯定出大事了。在去往甄妮處的的士上,金枝徑直撥通了120。一小時(shí)后,摟著深度昏迷的甄妮,身為職業(yè)川劇幫腔演員的她悲愴長(zhǎng)嘯:“你不是說(shuō)好要替滋滋活著嗎?只有你活著,滋滋才不會(huì)真的離開(kāi)!”七個(gè)七天,四十九個(gè)奇異的日子,甄妮很少合眼。金枝照料她的日常起居,她偶爾也照料金枝。那樣的時(shí)刻,是她把對(duì)方誤認(rèn)作滋滋了——金枝跟外甥女一樣大眼嫵媚,身材高挑輕盈。有天下午,甄妮從半山森林公園回來(lái),順路買(mǎi)了兩盒杭州糕點(diǎn),并要金枝一起去西藏:“我電話思密了……”林思密是她和滋滋在拉薩的房東,正宗壹江人,卻喜歡吃滋滋家鄉(xiāng)的桂花糕。她邊說(shuō)邊打開(kāi)衣櫥問(wèn)金枝:“明天你穿哪件外套,白鴨絨還是雙面羊毛呢?”更多的時(shí)候,她還是能夠認(rèn)清人的。金枝雖年長(zhǎng),但始終帶著不成熟的少女氣,性格活潑,卻沒(méi)有滋滋的靜謐淡定。她語(yǔ)速很快,不似滋滋溫軟斯文。
這套臨時(shí)租用的小居室,離滋滋入住的省腫瘤醫(yī)院只有三站路,客廳既是起居室也是臥室。甄妮常叼一枝玫瑰或百合,在布藝沙發(fā)上打坐,有時(shí)在狹小的空間里輕柔起舞——她從小在父親供職單位的培訓(xùn)班習(xí)舞,同時(shí)跟父親學(xué)書(shū)法。金枝是川劇演員,卻并不擅舞,只是從旁靜觀甄妮的舞姿:那是哀痛難抑的狂草,又像啼血悲鳴的琴音。這個(gè)生命里為情所困的女子驀然發(fā)覺(jué),自己是多么艷羨滋滋和甄妮的真摯情誼,如果她此時(shí)伸出手去,一定會(huì)像甄妮擁抱入殮時(shí)的滋滋那樣瘋狂,任有多少雙手也難以分開(kāi)。
“末七”第三日,金枝帶著甄妮登上了西去的客機(jī)。
系好安全帶,甄妮回過(guò)神來(lái),央求金枝放她下去:若不能繼續(xù)留在杭州,也要改簽機(jī)票,只要不回壹江就行。
看著甄妮恍惚憔悴的神色,金枝一時(shí)不知該說(shuō)什么。她許諾甄妮父親,要將他女兒平安帶回,可此時(shí)同行的已不是本來(lái)的甄妮——生死別離將一位年輕姑娘變得面目全非,那個(gè)豐潤(rùn)活潑的甄妮消失了,剩下的只是她的廢墟與夢(mèng)魘。
(節(jié)選自《催眠師甄妮》第一章)